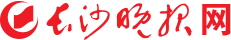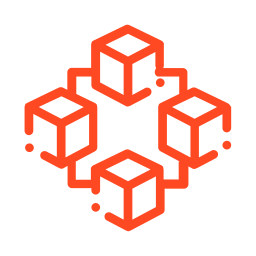那条乡路
袁长江
去很偏远的小山冲,是因为一位长辈与世长辞,在我们的家族里,她那一辈的已经屈指可数,生前她常念叨我的好,这让我感念莫名。
我只记得她家的大致方位,车子在狭窄的山路间蜿蜒而过,一点也不敢懈怠。一边是山,一边茂盛的柴草里,是一座不大的水库,路两旁的树木已经侵占了一部分路面,又无人砍伐。我没敢看蓄有多深的水,水库下游就是我的家乡,生息多年的小村落,至今仍有我的一亩三分地。村里水田的滋养全靠这座并不大的水库,水库蓄水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晚稻的收成,很多的时候都是水源有限。我常在深夜尾随在父亲身后,一路看守,将仅存的一点水放进田里,到水田放满的时候,每每已是日月交替时分。
正因为看水,这段路还算熟悉,再往里走便已是水泥路的尽头,遥遥可以听到山那一边有鞭炮的声响,已经不能再开车过去,我只好循着声音选择步行。
我有点迷失在这初秋时分,天地间还是夏天的模样,暑热并不曾消退半分。入眼皆是苍翠,一丝别的颜色也没有,重叠的、堆砌的绿似乎随时都会坍塌流淌开来,田塍也在其中,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田,或是躲藏在苍翠之间长满青草的水圳,或是行人太少,未曾硬化的乡路也是青草葳蕤。
我已经多时没有走过这样的路了!习惯了整洁的水泥路和柏油马路,一丝草屑都没有的精致,乡路是不好走的,道路狭窄,草木修长,一圈走下来,裤子就湿了,还挂满草屑和种子。
说是乡路,更像是田塍,黄沙泥水,早被踩得密实平整,只有野草顽强,几乎覆盖了所有路面。庆幸的是,田园并没有荒芜,正是碧绿原野的一分子,稻穗已经开始垂下头去,一如从前的诚恳与谦卑,恰恰是这个季节最好的收获,能在这个小山冲里见到连片的水田真让人感动。
沿着乡路行走,我有些失神,不知道自己去的方向对与不对,恍然之间又觉得自己像当年在田野上的少年,有风吹过,稻浪已经很有分量,不再被风随意摆布,我的脚步也变得踏实,一步一步,试图寻找当年走过乡路的感觉,草是柔软的,路却很坚硬,能感觉到每一粒石子的形状。我极想把鞋脱下来,曾经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赤脚在田塍上奔跑的,毫不在意小石子会硌到脚。路边有一大块红薯地,同样是铺陈的绿色,是谁和我有过一样的想法,明显有一处新鲜的黄土,一如当年我挖过的痕迹,是我?不是我!
鞭炮声越来越明晰,一阵紧似一阵,就在水田的那一头,乡路的终点之处。去世的长辈是我们这个家族硕果仅存的耄耋老人,一生要强,倔强而又自负,终究难敌时间的淘洗。她曾多次来我诊所里,寄望我能为她“撑腰”,可世情繁复,又岂是我一个远房晚辈能左右的?每每让她怏怏而归,只是觉得,人情练达,我还是做得很不够,需要用一辈子去学习。去年的这个季节,九十多岁的她还托人带给我一袋捡来的板栗,尤其让我诚惶诚恐,中间若有什么蹉跌,我可真的是罪莫大焉,无以洗脱。
乡路又变得稍宽,不远了。路旁的水井井沿长满了凤尾草,井水清澈,井里的天空毫无颜色,水里也是清澈无物。绿树掩映下的小院红红绿绿,热闹非凡,可以看到这里近乎最后的喧腾,很快一切就将恢复沉寂、冷清,直到萧然,墙垣倒塌……现在已经有很多小山冲里的人家归于消失,或搬迁或不再有人居住,房子须臾之间便被藤树掩盖。
我回头看了一眼刚刚走过的乡路,仍旧只看到漫漶的碧翠,在山风里恣意流淌。那条乡路已不复可见,是不是稻浪之间那一抹色差,我也不知道。唯一不变的是,不管它在哪里,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都是我来时曾经走过的路。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