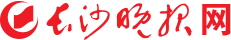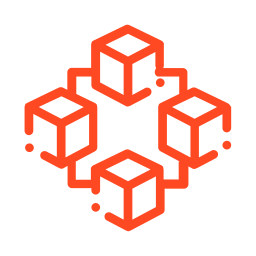阳光很盛
刘益兴
那年,我从长沙去云南,在那座海拔接近3500米的高山上,与孩子们度过了一年。因为他们,我成了老师,只过了一次教师节的老师。
我的一生都永远只有这十几个学生,而我的灵魂时常回望那个苍茫寂寥、雪山与烈日同辉,却有着真诚笑容的地方。那个往西经过福贡县,便到了中国与缅甸边境的,位于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小村庄。
几座巍峨的峻岭,任由微风轻抚,将山谷间的翠绿林海雕琢成翻滚的浪涛,那层峦叠嶂的绿意,曲线流畅而柔美,犹如少女的裙摆轻轻摇曳。月光是极柔和的,将那个山腰上的静谧村庄轻披上一层银纱,宛如梦境中漂浮的星辰之村。
在那里的多少个夜晚,我与篝火为伴,就在校园里那间昏暗的老房子中。外面或是风、雨也有时是雪,几根粗大的木柴在火堆里“哔哔”作响,散发着方圆几米内的温暖。
有火就有人,同校的本地教师雀老师常说这火是傈僳族人的必需品,如同一个古老部落的图腾。唯有在山野之上,火焰燃烧得格外温情,像是火红的心脏,在大地上永恒地跳动。夜色深时,村里家家户户都要燃着,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这间坍圮败坏的老房子是每个支教老师来校后第一晚都要过来的地方,大家围坐在火堆旁想着、谈着,一边将木柴投入火堆中去,让火焰染上更夺目的光彩,就像是一个虔诚的仪式。
老志愿者走了,新志愿者来了。如此生生不息,于此火光不灭。
大多数的时间里这儿都是艳阳高照,我常躺在教学楼对面的古树下,看着绿意盎然的林间空地上,孩子们在光影斑驳的树荫下奔跑嬉戏,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偶尔还有几个娃儿欲对树间奔走的松鼠下手。他们在曲折蜿蜒的小径上跳着、跑着,那满是灰尘的稚嫩脸庞上,总有笑容。
阳光很盛,万物都在闪闪发光。
极少数的时候山上才有雨,而大雨倾盆更是罕见。哪怕天际云层翻滚如沸,用不了多久也会有一束灿烂得耀眼的光芒由天而降,将满目萧瑟的雨景印染上了太阳的温柔与爱意。
孩子们在教室时就更闹腾了,在课桌上下翻滚着,又拿了扫把追逐打闹,整个教室像片喧嚣的森林。我时常觉得自己像是个手持魔法杖的老头,守在森林的入口,看着他们如草木般欣欣向荣地长大。
又是一年暑假了,也是离开那里的第十年,记忆中那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也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大人了。
雀老师写过一首诗,诗歌挺短,却带着他们傈僳族人的精神意志:
谁叫我们起的就是这个名——傈僳人
锤打千山的筋骨,怒吼万里的长风
一个躁动的民族,一群初生的牛犊
刀山闪耀着冷锋,火海呼啸着热焰,吼一声,大道坦途
吼一声,毅然地走出,阿爸的箐火
挣脱,阿妈的麻线
牵着山野的落霞,赶着大山的雄姿
我们来了!重重地敲开,紧锁的黎明!
那些孩子是否走出了群山的怀抱,去敲开城镇紧锁的黎明呢?
还记得走的前一天晚上,村里那些质朴的傈僳族人和普米族人来送别的方式。附近的村民来了有近三十人,在黑夜的学校空地里燃起篝火,大喇叭中放着民族音乐。
明月繁星下他们拉着老师跳起舞蹈来,他们称之为“跳脚”,穿着民族服饰,无论男女老少都相互拉着手,随着旋律欢快地跳着。跳脚的闲暇里还有敬酒,他们自带了酒来,一碗接着一碗。有村民唱着清亮的送别民歌,要下山去的老师与送别的人一一相拥,无语凝噎。
整整三个小时,村民们才离开。
多么怀念啊,在如今这偌大的繁华城市里只觉得缺点什么。让人有些许的孤独,那些蓝天白云,只有在黑夜的梦里才能醒来。
我们终于是不复再见了,我亲爱的孩子们……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