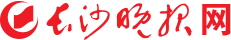散文 | 刘怀彧:蔸根火
“红薯饭,蔸根火,除却神仙就是我。”在今年过完冬至的那一天晚上,蓦然我就想起宁乡流行过的一句俗语,也想起老历年节离我们不知不觉又近了。
“红薯饭,蔸根火,除却神仙就是我。”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村谣,可见旧时的宁乡人对温饱的期盼和满足。
我想起乡下过年,最亲近的是一盆红彤彤的炉火。
我们宁乡一带把厨房叫炉子屋,也叫灶屋。这里一般有两个炉灶,一个土砖砌成的立灶,灶台灶眼灶门齐全,是煮饭炒菜的正规军;一个地上挖成的地灶,方形土池,上方悬挂黑黝黝一副梭筒钩,挂上铁锅水壶,可临时热饭烧茶。
地灶一方靠墙,其余三方可坐人,主要是烤火。来客了,竹椅板凳一挪,三人可坐,十人也可坐,只要中间有个火意思,圈子可以足够大。靠墙一方常会立个鞋架。我们宁乡旧时每到冬天必多雨,土质黏重,往往外出一圈,鞋子拖泥带水,像驾回来一条小船。进门后无分主客,鞋子往架上一挂,半个时辰即可烤干。敲掉泥块,往鞋里垫层干草,又可以出门上路了。
一面烤火,一面聊天,灶屋就成了冬天最热闹的场所。
于是村里就出现了一种“蹭火专业户”。比如坤叔,无父无母无妻儿,便成各家各户的炉边常客。上家熄了去下家,西家熄了往东家,哪家火旺去哪家。除了蹭火,自然还蹭饭。从除夕到元宵,乡人生活无非请客走亲。但凡请客人家,不在乎多双碗筷。半月下来,瘦弱的坤叔不觉长了一层膘,忽然腰圆体壮,显出几分英武。
在我们乡下烤火,最暖人最享受的,是大树根生出的火,吾乡称为蔸根火。它绵厚持久,散发着特别的馨香,尤其便于储火。灰土一掩,人走火熄。一有客来,拨开灰稍稍一吹,又熊熊满堂。
可到我略懂人事时,木头已极为难得,蔸根更是罕见。
大炼钢铁后,林木尽毁,遍山枯瘦。日常做饭,要么是稻草,要么是从山里耙回来的松针落叶。这些柴火太不经烧,一大把塞进来,哧的一下就尽了,不仅烧火受罪,而且烟尘滚滚、满屋落灰,烤火也难受。
可吾乡普遍好客,讲究“客进旺家门”。若家有来客,没地烤火,东一个西一个,没得氛围,留人不住。所以柴火难求时,讲究一点的人家就引进了蜂窝煤,可当年那东西不仅金贵,而且没得明火,还气味呛人,同样不适合围炉烤火。
这时节,哪家有个蔸根,过年就特别硬气。热气在屋顶上持续升腾,如同吉祥的信号,招来满屋乡邻,这家就特别旺相了。正因如此,各家都特别留意树桩,一旦发现,就赶紧挖走。有心的人家,一年下来,小小的,总能积攒几个。
有一年,我家忽然有了个大树蔸。老虎一样蹲在屋檐下,引来很多人的羡慕赞叹。树蔸是从坤叔家拖来的。坤叔屋后有个陡崖,原来一直靠这树蔸撑着。一场秋雨,终没撑住,连土带蔸压在后墙。坤叔已外出打流,幸得父亲发现,帮他挑土通沟,护住了房子。大树蔸,就被父亲顺了回来。
那年春节,全村数我家最红火。整个正月,大蔸根一直满身披红带火,有时还嗤嗤发笑。炉火笑,客人到。首先是坤叔远游而归,因为贡献了一个大树蔸,他理所当然就成了我家一主,端茶送水,大声大气地招呼客人炉边就坐。倘若有人夸赞这炉红彤彤的蔸根火,坤叔更加神采飞扬,不免将这树蔸来历一一细说,一副豪气干云、居功至伟的样子,大家止不住呵呵发笑。
这年正月,我家果然客流不止。外出多年、断了音讯的姑姑,突然在正月初六寻回老家,还带来我两个漂漂亮亮的小表妹,五亲六戚,尽来看望,一向寒色皑皑的茅草屋顿时欢天喜地。
坤叔更是满脸红灼,直把越来越瘦的大蔸根,说成了舍身济世的观世音。
就在这年,坤叔被我家一客人瞄上,经父亲母亲加以拾掇,成了一户好人家的上门女婿。
>>我要举报